金道原创 | 新公司法背景下股东会职权转授权范围的研究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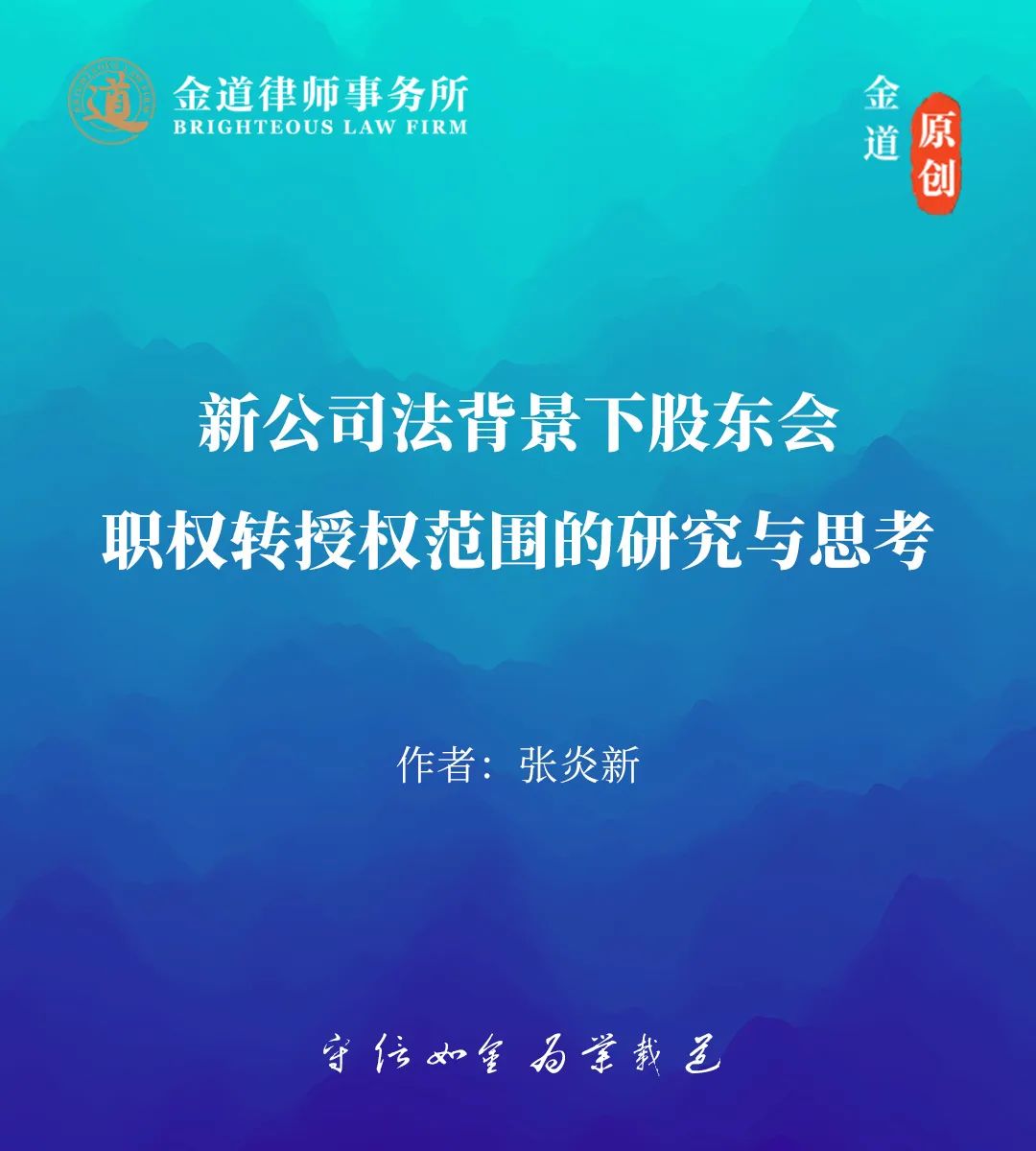
关于董事会的法定权限,本法第六十七条(针对有限公司)和第一百二十条(针对股份公司)以列举的方式有明确规定。然而,问题在于第六十七条第2款第(十)项“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中究竟哪些原属于股东会的职权可以依据该规定转授权给董事会行使?
根据本法第五十九条第1款列举的共九项股东会法定职权中,第(一)-(三)项明显属于具有类似授权人自身属性特有的权限,即董事会不能自己选举和更换其董事会成员,也不能自己审议批准自己作出的董事会报告等。因此,在法理上前三项职权不具有转授权的可能。而对于剩下的第(四)-(八)项明确列举的股东会职权,从内容表述上均不属于专属于股东会的职权,理论上似乎存在转授权的可能性。
然而,笔者关注到该条第2款单独规定了“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该内容特指本条第2款第(六)项权限,但并无对其余第(四)-(五)以及(七)-(八)的权限是否可转授权有明确的表述。
因此,如何理解该条第2款,成为确定股东会转授权范围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笔者检索的特拉华州商事法庭最近的一项判决中,法院认为,“可以”(May)一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够表示强制性,尤其在自由选择情形受限的情况下1。一般来说,选择情形受限的程度越大,“可以”作为强制性的语义就越明显2,否则这种特定的受限就会没有意义。如考虑该表述“A可以将股份出售给B”。从字面意思看,人们通常会认为A可以将股份出售给任何人——此处只是明确提到可以出售给B。但进一步思考该表述的用意会发现,该表述限定授予股份的对象为B,这是一种严格限制可选择情形的表述。如果双方在授权A出售股份时只提到了B,那是因为A被禁止将股份出售给任何其他人。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要特别且仅单独提及B作为授予对象。在解释“可以”一词时,必须给予这种选择受限的用意以合理的权重。因此,在这种非常明确的选择情形下,“可以”被理解为强制性规定可能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在法律条文中,前述例子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当被理解为立法者的意思表示。回到本法第五十九条第2款,立法者仅仅单独且明确规定的可授权对象为“公司发行债券”这一特定内容,这就必须给这样的立法安排赋予一定的用意。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许可(即包括但不限于的解释),那么在逻辑上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单独提及这一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此处“可以”一词的解释,应将其理解为强制性(而非许可性)更妥,即股东会转授权范围仅限于“为公司发行债券”的相关决议(即解释一)。
如果将“可以”解释为强制性规定,那么意味着股东会可转授权的范围仅限于“为公司发行债券”,这可能与本法其他条款存在矛盾。如本法第六十七条第2款第(十)项规定,董事会可行使“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如果按照解释一的理解,此处的“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仅限于“为公司发行债券”。如果仅仅为了这一个职权,用如此概括性的表述来规定董事会的职权,似乎显得“小题大做”。
这种矛盾更为明显地体现在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即“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董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规定虽然属于股份公司章节,但因本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本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有限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因此,前述第一百五十三条中提到的“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表述,可以对应本法第五十九条第1款第(五)项(即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换言之,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本法后文(第一百五十三条)直接表明了股东会转授权的范围至少还包括发行新股(即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那么这样就明显突破了第五十九条第2款规定的“发行公司债券”的转授权范围,从而与解释一构成体系解释上的矛盾。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中对本法第五十九条的理解表述来看,“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部分职权,不应破坏公司基本的治理结构,打破两者的平衡和制约关系,尤其不能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3。该表述应当被理解为对股东会转授权范围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反向理解之,即如果转授权的行为可能构成破坏公司基本的治理结构,特别是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那么该转授权就不应当被允许。该书作者通过以本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即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为例加以论述。显然,该款规定,以“应当”一词强行限制该职权专属于股东会,因而不能转授权给董事会,否则可能会破坏公司的基本治理及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书作者虽然仅阐述并举例哪些条款不能被股东会转授权(基于违反公司基本治理的底层逻辑),但我们可以合理得出的结论是,有相当一部分股东会职权(至少不应该只有1项)是可以被转授权的,否则作者就无需大费周章地论述不能被转授权的内容,而只需单独正面阐述具体哪几项股东会职权可以被转授权。
事实上,立法者对于股东会转授权范围的谨慎态度侧面反映了对我国公司治理现状的容忍度和开放度。传统观念中立法者总是希望通过法律强制性规定为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划清界限,以免出现大股东通过转授权给其实际控制的董事会而过度操控公司的局面。然而,除了个别明显违背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高危”领域(如对本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担保)等,立法者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这也是公司法的核心原则。至于对于公司大股东通过转授权股东会职权给董事会进而操控公司的担忧,这可以通过事后救济手段(如诉诸本次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大量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的信义义务的约束以及第二十一条关于股东滥用权利的限制)来加以规制,这也是董事会职权主义的精神所在。笔者认为,这种事先尊重公司意思自治以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事后通过强监管对相关董事课以较高的信义义务责任的做法,充分平衡了尊重公司意思自治和保护中小股东不受大股东侵害的利益考量,也应当是今后司法实践中对类似争议应当充分加以考虑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1.Salama v. Simon(C.A. No. 2024-1124-JTL)p.35,https://cases.justia.com/delaware/court-of-chancery/2024-c-a-no-2024-1124-jtl.pdf?ts=1732767686
2.Kenneth A. Admas, A manual of Style for Contract Drafting §3.212 (5thed. 2023)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
4.李建伟,《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
律师简介
PROFILE
张炎新 律师
业务领域:跨境投资与并购、国际贸易争议解决、公司商事领域
教育背景:
宁波诺丁汉大学 学士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金融和投资硕士
工作经历:
张炎新律师曾在某大型政策性金融央企从事跨境贸易风险管理工作,对跨境贸易及相关投资风险有深入了解,为客户提供跨境贸易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多年来深耕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相关争议解决领域,尤其在国际贸易买卖合同,无单放货,海上货运代理及保险等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当前主流的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CPTPP等)有深入研究。
张炎新律师已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律师执业资格考试,进一步提升及优化其在英美法系背景中的跨境争议解决能力,并参与多起国际商事仲裁争议案件。
联系方式:
手机:13676885880
邮箱:zyx@zjbl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