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观察 | 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谈重大疾病保险纠纷中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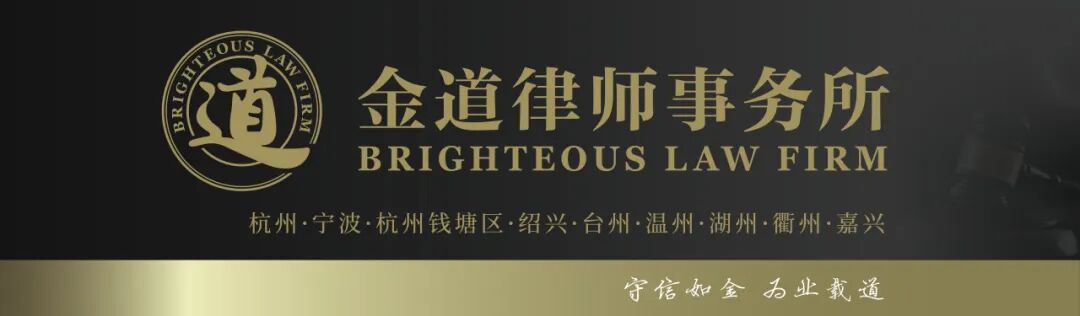
前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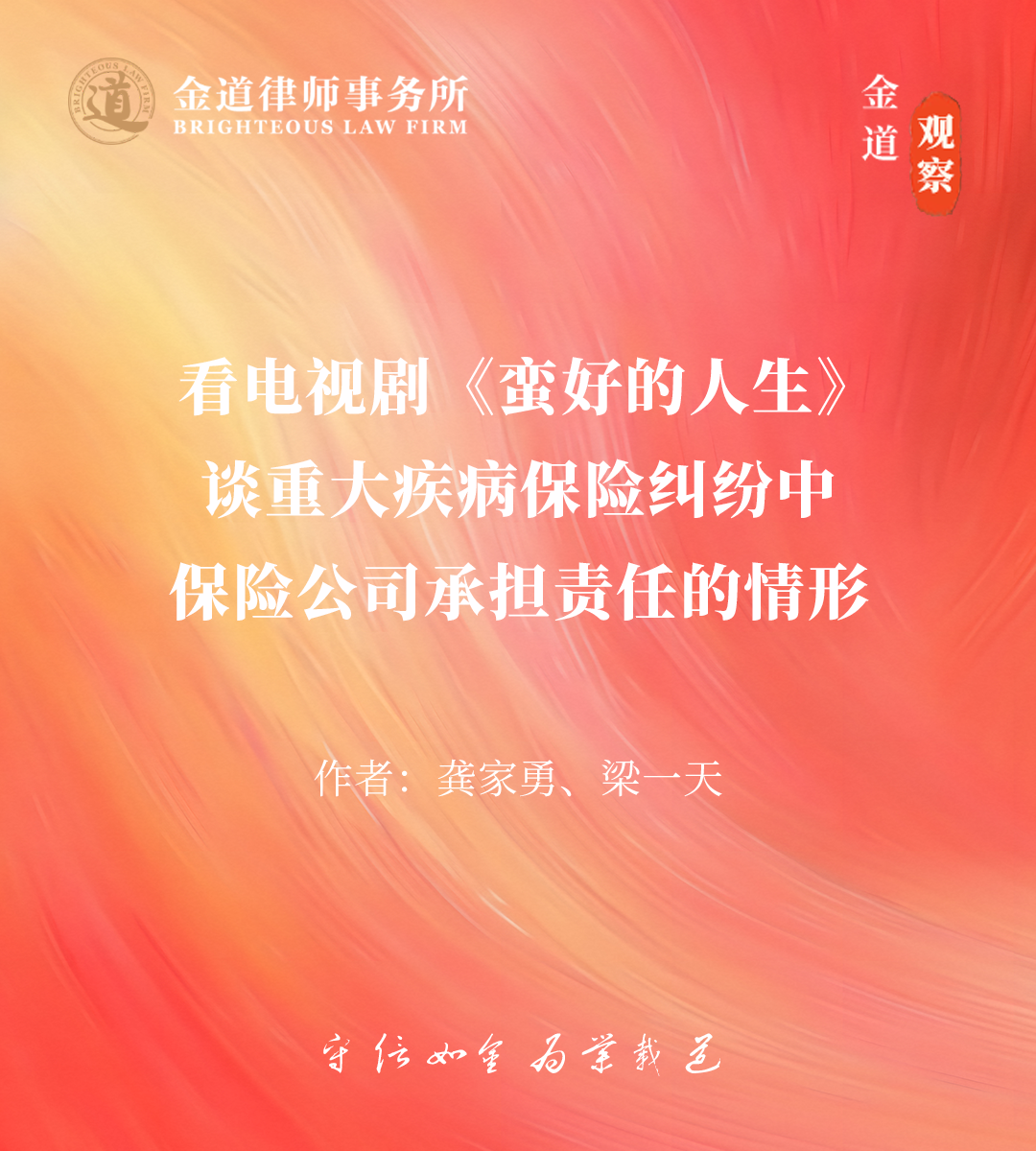
孙俪、董子健主演的电视剧《蛮好的人生》于2025年4-5月播出,该剧是以保险行业为背景,孙俪饰演的胡曼黎是保险金牌销售,董子健饰演的薛晓舟怀揣理想踏入保险行业,剧中各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公司、保险销售人员相互交织,演绎出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
该剧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很多保险行业知识,笔者注意到剧中的重大疾病保险相关法律问题,和律师日常办案遇到的情形有相似处。重大疾病保险作为人身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被保险人提供经济保障,减轻因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在实际理赔过程中,保险人(即保险公司)与投保人(或受益人)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往往涉及保险条款的解释、理赔条件的认定以及保险责任的界定等问题。
本文从诊断方式争议、免责条款效力、如实告知义务等常见纠纷类型切入,结合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的典型案例,分析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逻辑,为投保人维权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重大疾病保险 保险纠纷理赔 保险拒赔 保险责任 格式条款
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重疾险”)指被保险人患有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达到的疾病状态或进行的手术,由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商业保险形式。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颁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年修订版,2020年11月5日实施),重疾险保障的疾病范围应当包括该规范内的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如果保险产品还保障了保险金额低于前述六种重度疾病的其他疾病,则还应当包括该规范内的恶性肿瘤——轻度、较轻急性心肌梗死、轻度脑中风后遗症。除前述疾病外,保险公司可以选择使用该规范疾病范围以内的其他疾病。
重疾险合同中往往包含复杂的条款,如等待期、免责条款、诊断方式等,这些条款在实际理赔中可能引发争议甚至是诉讼,而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与否,往往有规律可循。
一、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判例研究
(一)被保险人的诊断方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选择合同约定以外的治疗机构,保险公司仍承担责任的判例
案例1:苏某与某健康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京74民终717号判决中,苏某被诊断为甲状腺癌,但未按保险合同要求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而是通过“细胞学检查”确诊。苏某申请理赔后,保险公司以不符合合同条款为由拒赔。
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必须以“组织病理学检查”作为确诊标准?保险条款中关于诊断方式的约定是否有效?
法院审理认为诊疗方式选择权属于医疗机构,保险公司不得通过格式条款限制合理医疗手段。合同条款要求“组织病理学检查”加重了被保险人义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属于无效条款。苏某的诊疗过程符合医学标准,应获赔付。
另外,笔者注意到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9年第3号《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应采纳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版《诊疗指南》明确细胞学检查为常规手段,保险公司不应以合同条款排除新技术。通过“细胞学检查”方式确诊的诊断结论科学严谨,符合轻症疾病定义,从这个角度,保险公司也应赔付。
案例2:石某与某保险深圳分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3)粤0303民初22890号判决中,石某因白血病在非合同约定的医院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治疗,保险公司以“非认可医院”和“非必要费用”为由拒赔。
本案争议焦点为紧急情况下转院是否合规?外购药及第三方检测费用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患者因病情危重转院符合“紧急就医”例外情形,医院委托的检测费用及必要外购药属于合理医疗支出。并且,保险公司未充分提示免责条款,相关条款无效,应全额赔付。
(二)对等待期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判例
案例3:高某与某保险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苏0106民初3158号判决中,袁某作为投保人在2012年以高某为被保险人投保某终身重疾险,因袁某未按期交纳保险费,保险合同中止,袁某于2023年5月2日补交了保险费,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于2023年5月2日起复效。2023年10月16日高某确诊甲状腺恶性肿瘤,并于当月19日治疗结束出院。后高某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复效后180日内确诊重大疾病”的免责条款拒赔,并主张解除合同退还现金价值。
本案争议焦点为复效后180日免责条款的效力及保险公司是否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一者免责条款未通过加粗等显著方式提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义务,条款无效;二者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履行提示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故需按合同约定赔付保险金(扣除已退还现金价值)。
案例4:金某与Y某人寿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浙0521民初1671号判决中,原告金某2019年投保两份重疾险,2023年确诊肺恶性肿瘤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等待期内(180天)确诊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CIN Ⅲ)属于轻症重疾为由拒赔。
本案争议焦点为CIN Ⅲ是否属于条款约定的“原位癌”及轻症重疾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相关条款未明确将CIN Ⅲ定义为原位癌,且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疾病属于轻症重疾范围。免责条款未通过显著方式提示,未尽说明义务,条款不生效;且前后疾病无关联性;综合各方面原因,保险公司应赔付。
(三)投保人虽未告知,但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付责任的判例
案例5:焦某与某保险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苏0104民初2100号判决中,焦某于2020年1月投保某寿险公司的终身寿险及附加重疾险,2023年4月确诊多发性脑梗(符合合同“轻微脑中风”条款),申请轻症保险金及豁免保费时,保险公司以其2018年曾检查出“右侧顶叶点状脱髓鞘病变”(投保时未告知脑部疾病)为由拒赔。焦某主张投保单中的“脑部疾病”属概括性条款且未具体询问,诉请支付保险金。
本案争议焦点为健康告知中“脑部疾病”的概括性询问是否有效?投保人是否未如实告知既往脑部病变?
法院审理认为“脑部疾病”条款未列明具体病症,属于概括性询问,不构成投保人告知义务;脱髓鞘病变仅为影像学诊断,无确切疾病证明,与脑梗无直接关联;故保险公司应赔付。
案例6:王某与D某财产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浙0502民初1432号判决中,王某于2021年12月首次投保百万医疗险,2023年1月续保后确诊结肠癌(符合“恶性肿瘤-重度”条款),故申请医疗费赔付。保险公司以首次投保时隐瞒“乙肝病毒携带者”病史为由拒赔。王某辩称续保时未重新询问健康状况,且乙肝与结肠癌无关。
本案争议焦点为续保时未重新询问乙肝病史是否影响理赔?免赔额条款是否有效提示?
法院审理认为续保视为独立合同,保险公司未重新询问健康状况,不得以首次投保未告知事项拒赔;2023年保单未载明健康告知内容,保险公司未尽提示义务;故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案例7:曹某与某健康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苏1291民初86号判决中,曹某于2022年6月投保少儿重疾险及附加豁免保费险,2023年6月确诊甲状腺癌(符合合同“恶性肿瘤-轻度”),要求豁免后续保费。保险公司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盆腔炎、肝血管瘤”等病史为由拒赔并解除合同。曹某主张保险公司未具体询问病史且未告知事项与甲状腺癌无关,诉请继续履行合同。
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是否对健康事项进行有效询问?未告知病史(盆腔炎等)是否足以影响承保决定?未告知病史与甲状腺癌是否存在关联性?
法院审理认为电子投保页面快速跳转且未逐项询问,视为未履行有效询问义务;保险公司未证明盆腔炎等病史与甲状腺癌存在关联,解除合同无依据;甲状腺癌符合合同“轻度疾病”定义;故判决继续履行合同并豁免后续保费。
(四)投保人所患疾病与保险条款规定的疾病表征不符,但保险公司仍承担责任的判例
案例8:葛某与某保险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在(2024)苏1322民初4971号判决中,葛某于2019年投保某重疾险,附加中症疾病保障。2022年其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需长期使用生物制剂阿达木单抗治疗。保险合同约定“中度强直性脊柱炎”需同时满足:(1)严重脊柱畸形;(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完成六项基本生活活动中的两项。葛虽被诊断为“高病情活动度”,但脊柱活动度正常,未达条款标准。
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条款对中度强直性脊柱炎的限定是否合理?保险公司是否尽到条款说明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条款设置的“脊柱畸形+生活能力丧失”标准超出医学对中度疾病的界定,属于不合理限制;免责条款未以加粗、单独说明等方式提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条款无效;葛某病情符合医学上的“中度活动性”标准;故判令保险公司赔付。
案例9:孙某与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
在(2024)京74民终862号判决中,孙某投保重疾险后被诊断为左颞枕颅骨嗜酸性肉芽肿,并接受开颅手术。保险合同约定“良性脑肿瘤”属于重大疾病范围,但未明确肿瘤定义。保险公司以嗜酸性肉芽肿不属于肿瘤且疾病编码与《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不符为由拒赔。孙某主张病案中疾病编码对应ICD-10中的“动态未定肿瘤”,应视为符合条款约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嗜酸性肉芽肿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良性脑肿瘤”?保险公司对肿瘤定义的解释是否有效?
法院审理认为依据ICD-10将嗜酸性肉芽肿归类为“动态未定或动态未知的肿瘤”(编码D47.7),认为其属于保险合同意义上的肿瘤范畴。保险公司虽提交医学文献主张该疾病非肿瘤,但保险合同未对“肿瘤”作出明确定义,且ICD-10作为权威分类标准具有优先参考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不利解释原则,条款争议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法院结合孙某接受开颅手术的事实,认定其符合“良性脑肿瘤”的治疗条件,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
案例10:朱某与某人寿保险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在(2024)浙0702民初3644号判决中,朱某投保三份重疾险后因爆发性心肌炎导致心搏骤停,抢救期间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5分,并持续使用呼吸机及ECMO超过96小时。保险合同约定“深度昏迷”需同时满足GCS≤5分和使用生命维持系统96小时以上。保险公司以朱某在后续治疗中GCS评分恢复至9分以上为由拒赔,主张其昏迷状态未持续达标。
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合同对“深度昏迷”的定义是否要求GCS评分在96小时内持续≤5分?原告病情是否符合条款约定的疾病状态?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条款中“持续使用生命维持系统96小时以上”未明确要求GCS评分在96小时内全程≤5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格式条款存在歧义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原告在抢救初期GCS评分为5分,且使用生命维持系统超过96小时,已满足条款字面要求。保险公司主张需全程维持低分缺乏合同依据,法院认定其拒赔理由不成立,判决全额赔付。
二、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要点归纳
(一)特定情况下,保险公司不应以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诊断方式或治疗机构为由拒赔
1.在保险合同中关于重大疾病诊断方式的争议中,核心矛盾集中于保险公司是否能够通过格式条款限定具体的医疗检查手段或者指定的治疗机构。例如,部分合同要求必须采用“组织病理学检查”作为确诊依据,但实际诊疗中医疗机构可能根据病情选择更高效的“细胞学检查”或其他新型技术。 此类条款的效力问题成为关键,若条款内容排除了通行的医学标准或单方面加重被保险人义务(如强制要求特定检查方式),则可能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关于“格式条款公平性”等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
2.同时,保险公司对诊断方式或机构的限制性条款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法院在审查条款时强调,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负有充分提示说明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条款不产生效力。
3.在紧急就医场景中,患者因病情危重选择非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只要诊疗行为符合医学必要性和合理性,保险公司不得仅以“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拒赔。若能达成同样治疗疾病目的,允许被保险人选择对自身损害较小的方式进行治疗当属应有之义。1所以,对于紧急就医情形,司法实践倾向于保护患者权益,只要医疗行为基于病情需要且费用支出合理,即使涉及外购药或第三方检测,仍可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4.从司法裁判逻辑来看,法院以尊重医学诊疗自主权为基本原则。医疗机构根据病情选择最优诊断方式的权利不受保险合同条款的不当限制,尤其是在医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僵化的合同约定不得阻碍新技术的应用。例如,2022年版《诊疗指南》明确将细胞学检查列为甲状腺癌常规诊断手段,保险公司若继续沿用旧条款排斥该技术,则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二)保险公司若未对等待期条款尽提示说明义务,则该条款不具有效力
1.等待期条款通常规定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如90天或180天),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该条款的目的是防止投保人带病投保,同时应对疾病潜伏期问题。等待期的设置符合健康保险合同的订立目的,有利于防范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但在实践中常为保险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并没有选择拒绝接受或修改条款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合同的全部内容。2因此,等待期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认定为格式条款,保险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先合同义务,包括明确告知条款内容及公平解释条款目的。
2.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以及《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对保险责任等待期作出明确告知。在实践中,等待期条款的设置和表述不尽相同,有些具有明显的“等待期条款”字样并单独成条,还有的与疾病定义、赔付方式等融合在一起,难以识别。3若等待期以疾病定义和释义的方式订入合同,即便不认可其为一种免责条款,在健康保险中此种条款为专属特殊条款,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免责条款。4
同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的义务。若等待期条款单独成条,保险公司证明已附有加粗、加黑等方式,则可证明其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若等待期条款并不能直接识别,则保险公司需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例如提供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免责条款确认书》、对法律后果具体解释的录音录像等过程证据。
3.“等待期条款”与保险事故的关联性亦需严格审查——若等待期内疾病与后期确诊疾病无直接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不得扩大免责范围。
(三)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边界
对于保险公司主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仍需承担赔付责任的判例中,核心裁判逻辑如下:
1.保险公司未充分履行询问和说明义务。在一些判例中,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未对投保人健康状况进行具体询问,免责条款仅以视频快速切换形式展示,无法证明已明确说明、询问。另外,投保单中概括性询问缺乏具体内容,不构成具体询问。这些情形都不构成保险公司充分履行询问和说明义务的情形。
此类案件的法律依据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以保险公司询问为前提)、第十七条(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及司法解释对“概括性询问无效规则”的细化。
2.保险公司未证明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关联性。如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告知某疾病史拒赔,但未举证该疾病史(如乙肝病史)与确诊的重大疾病(如结肠癌)存在因果关系,则保险公司以投保人隐瞒某疾病史为由拒赔不能成立。假如投保人虽然未如实告知,但未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并无因果关系,保险人拒赔就与投保人的情感需求和情绪体验是大相径庭的,也不符合保险实践以及保险原理。5
3.格式条款的严格审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四)限定投保人重大疾病认定的疾病表征条款或属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条款不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确立不利解释原则,要求格式条款争议按通常理解解释,存在歧义时偏向被保险人。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强调疾病诊断标准应符合通行医学标准,保险公司不得以自定标准对抗医学共识。
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严格审查条款的合理性,若条款定义的疾病表征明显严于医学通识(如葛案中将“中度”疾病设定为“极重度”标准),或未明确关键术语(如孙案中“肿瘤”无定义),则可能被认定为免责条款或作不利解释。相关判例的裁判逻辑体现为“医学标准优先”和“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保护”,即保险公司不得通过条款设计不当转嫁风险。
此外,保险公司常依赖格式化的“声明及授权”条款主张已尽提示义务,但法院更关注实质履行情况,如销售人员是否实际解释保险条款、免责内容,相关条款内容是否显著标识等。
三、总结
重大疾病通常伴随着高昂的治疗费用,而重疾险的保险金可以用于支付这些费用,包括手术费、住院费、药物费等,替代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部分或全部经济损失,帮助个人或家庭的正常生活。
但是,重疾险的投保、理赔并非一帆风顺,至少存在三方面道德或法律风险:
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并不符合重疾险的投保或理赔条件,却进行了投保或理赔,甚至是恶意骗保,损害保险公司的权益;
二是保险公司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对于应当给予投保人(或受益人)理赔的情形却不予理赔,损害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权益;
三是保险销售人员为了多做业绩,对不符合重疾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给予投保,或向投保人作出不实的说明、承诺,这样既损害了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权益,又损害了保险公司的权益;
就如上三方面道德或法律风险,因为更多情况下投保人(或受益人)是弱势的一方,故笔者的粗浅研究先着眼于重疾险纠纷中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
当投保人(或受益人)、保险公司发生争议甚至诉讼时,高度相似的判例可供参考,有助于司法机关公平合理地划分保险利益和责任。就像孙俪、董子健主演的电视剧一样,公正的司法裁判可以厘清保险纠纷,有助于构建“蛮好的人生”,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注:梁一天,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硕士,本所实习生。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内容仅供参考。如需转载或引用文章任何内容,欢迎私信沟通授权事宜。

